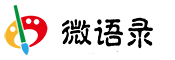(一)
头上的知了和太阳一样,不停地忙碌着。
山里的院门不锁,用段绳子系住就或者用根木棍别住就可以了。哪家大门敞着,槐树下必定有个戴花镜的老妇人,老人也就是做些缝缝补补,有时也为自己或者老伴做寿衣,这里的老人总是亲手给自己准备好衣服。做寿衣多是自己一针一线地缝,有的衣服上还要绣上花,多是龙或凤或祥云的图案。有时也拿起衣服自己比划几下,看不顺眼就拆了再做,有时也找几个老人一起做,相互帮助一下,可以做得更好。老人做这些衣服就像做其他的没什么两样,总是坦坦荡荡地。
山里也热闹,最热闹的就是喝喜酒,山里人喝酒需要实实在在的名目,儿娶女嫁打墙造屋就是最好的名目。
院子里灯火通明,大八仙桌子配太师椅子;小八仙桌子配着小马扎,远处是一溜临时砌的灶,风葫芦呼呼地吹着,火苗一个劲舔着锅底,锅里是大块的肉翻滚着,肉香弥散在空气里。
人齐了,长者坐在大八仙桌上,没什么祝酒辞,就是抿口酒挟口菜,一板一眼地。酒过三巡,有些老年人就吃饭了,老年人来了,也似乎只是一种仪式。不久,老人就三三两两的走了,热闹也就出来了。年轻人就热闹了,有故意说炒菜不好吃,也有故意说炒菜太咸了,咸死卖盐的,那忙碌着炒菜的人自然接话说,甚至提溜着大铲子赶到桌子旁,于是哈哈大笑一番。菜是大鱼大肉,油腻腻的,酒是乡村的酒,倒进喉咙,一股辛辣就冲上来,喝猛了就喘不上气来。年轻人分成两拨划拳,两个对阵的划拳,其他人负责喝酒,笑声和骂声就在你赢我输地较量中升腾起来,在院子上空回荡着。
夜深了,每个人的脸在酒和灯光下便成了紫红,自然跌跌撞撞地散去。
平静的生活还是像湖水会起涟漪般打破了,而今,破碎得一地凌乱!
搬出了山里,似乎连根也拔起了,山里就成了我再也回不去了的故乡了!
(二)
夏日农闲时,会有说书的来村子里。说书人多是盲人,师傅领着徒弟,三两人结队,手拿竹竿戳着路面走,肩上背着一个鼓,鼓细长,有半人高。
月亮升起来了,大树下,或石碾旁。早有人挑井水洒地上吸了热气。拿小马扎的,拎张破席的,都来了,围着说书人坐下。鼓,空空空的响,和着杨家将或岳家将的东征西杀。现在想来,鼓声就是个点缀,这点缀仿佛说书人的欲望:简单,纯净,朴实。说书人容易满足,给饭吃,给个地方住,临走时,给点干粮就行。
说书人记忆力好,声音也好听,一人说累了,另一个接着,丝毫不差。
男人们坐马扎吸旱烟,烟头一闪一红,便有和着汗味的烟草味飘散开来。女人坐席上,摇着蒲扇,乘凉也赶蚊子,孩子正枕着女人的腿呢。
鼓点和着说唱声,在夜空散开了。月光下,山影里,整个村子狗不吠,人不走。
孩子睡了。后来,女人哈欠连天了,大家也就散了。
白日里,也有叫卖的声走街串巷。卖瓜的,放下担子,抓下草帽子,边忽闪边喊:甜瓜喽——甜瓜喽。也有 “戗——剪子磨——菜刀吆”声,粗犷,绵长,半截村子都听得到。磨菜刀?乡人不会花那冤枉钱。刀不快了,顺手在缸沿上来回蹭几下就行了。剪子钝了,刨刀钝了,非得找他们不行。据说,京津一代,这行业用十几个铁片子串成串,手一摇,声可穿门透户入深闺。这铁叶子就叫“惊闺”,确实形象。大喊大叫,即使能穿门透户入深闺,喊一天,估计没人能行,也会惹人烦。
卖瓜的,戗剪子的,多是临近的人。用响器的人多是远处的。山里人称他们吃开口饭的,也总以为走街串巷的人混口饭吃不容易。
细细想来,山里的叫卖声,倒是透着一种相互体谅的意思,响器一响,或喊一嗓子,就知道什么人来了,用不着南腔北调地喊,也算得上是闻音知意了。
山里,因了这叫卖声而至今难忘,毕竟大多时候山里是个清苦而寂静的世界。
(三)
峰峦如聚,苍黛处如浓墨点染,岩石处寸草不生,生硬得很。后来见到老张,一下想到这岩石恰如山里汉子的肋骨,结实得显而易见。
果不其然的山区,北方的山区。
峰回路转,车如波涛上的船,索性坐起来,一只脚蹬着窗户,一只脚顶着前面的座椅靠背,这样省劲,不用死死抓着椅子靠背。窗外,山连山就成了波浪,脊和谷起起伏伏的,山尖倒是有些独特,直上的山体突然平了起来,恰如成长的山突然刹了车,造了一个平台,我是孩子的话,一定会想那是天仙舞蹈的地方,一个远离天庭却与凡间也有相当距离的地方最适合天仙舞长袖了。这是崮,沂蒙山区特有的地貌。崮顶全是硬硬的岩石围成,岩石似乎一下有了性格,劲道得很。
数到第八十七座山头和第七个崮时,车停了,见到了张军,一个瘦高个,略显腼腆的大男孩,还有男孩的父亲,后来我叫他老张的张大富。他有着魁梧的身躯,披着汗衫,汗衫下是强壮的筋骨,山里汉子的模样,是素描的好材料。和男孩自然地握了手,我伸出去的手在老张那里变成了一句话:刚忙完,没洗手呢。我知道山里人尤其是年纪大的人不习惯握手,其实老张也就四五十岁的年纪,可容貌要比年龄老些。
山脚下,几十户人家沿沟沿一字摆开,北方少见的布局。抬头,又是一崮。奶头崮,绝妙的象形,恰如少妇的乳房,挺拔,圆润。又长着一色的树,远望去恰如皮肤上细密的绒毛。第一次仰望它,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冲动在头脑里盘旋,甚至有些眩晕,自以为不是一个随意可以被震惊的人。似乎是来自母腹的胎动,又似乎是某种专注的渴望。。。。。。久久凝视它,知道除了记住它,我无计可施,素描显得粗糙拍照就更呆板了。
后来,每每有人问起沂蒙山的崮是什么?我就悄悄告诉,见过乳房吗?
女性的神秘之处,就这样坦荡在天地之间,静穆,坦荡。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耕种,仰望,口传着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仙女很善良,和崮下打柴为生的山民演绎了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只是结局不一样,善良的山民从来不喜欢悲剧。仙女一家去天庭了,临走,手一挥这里多了一崮,形如乳房,护佑着这里的人繁衍生息,据说现在崮下添了丁口的人家还要在山下跪拜一番,系上红绳呢。
进了村,进了院子就是吃饭。竟然吃了鸡,喝了酒。小鸡炖蘑菇,酒也冲,除了烈性,就是一股粮食糟了的味道在空腔里回旋,这是此前所没有的味道。多年以后让我想起这顿饭,更感觉那滋味的纯美,和奢侈。工业的发达总是会让人舍弃繁琐的程式去追求快速达到目的的手段,现代社会里,在许多方面,人们没有那份耐心了,那种一天天过日子一天天做活的耐心没了,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老日子在今天飞奔起来,如陀螺一般挟裹着人前行,那一招一式一板一眼地手工工序迅疾衰老了,抛离了,像曝光的胶片扔在墙角,落上尘,蒙上灰,在不经意间随着生活的零零碎碎彻底消失了。
厚道的山里汉子有个勤快的老婆,没多少言语,见了我进院子笑了笑,说:家来了?麻利屋里坐(来了,屋里去坐的意思)。转身去忙碌着盛菜烫酒了。等我们坐下来,她还在院子里忙着,无论我怎么坚持让她一起吃饭,她都不肯。直到喝酒说起这件事,才知道山里人家来了客人,女人是不上桌一起吃饭的,要随时添菜上水,照应着。看着这父子两个坦然自若吃菜喝酒,我总不能安心喝酒吃菜,这待客之道很真诚,还是让我恍如隔世的感觉。三个男人喝着酒,说着话。老张很能干,有果园,有大车,还是村委里的人。可他称呼他的老婆是屋里的,老张连老婆这个词语也说不惯。
听着山里汉子的女人忙碌的声音,还有远处不时的狗吠。抬起头,满眼的是黝黑的山林。
坐在院子里聊天,老张的女人去屋里吃饭了。
月亮升起来了,院子里清亮了,因了这月色和主人的收拾,墙外的远处是山,静穆中有些幽深,在月光里,反倒多了些迷离。
(四)
独坐也好。
树荫下,一丝丝扫帚纹上印着几许光斑,十几只小鸡仔还没小孩子的拳头大,整个一个绒球,细看去分明黄绒红嘴,吱吱叫着,走着,扫帚纹上便多了些细细的“个”,如风中竹叶纷乱。
摊开本书,席“蒲团”而坐。蒲团,山里的一种坐具。秋日采河边蒲苇,拧成绳,以绳编结成团垫,有二十公分厚,再以棒槌反复捶打,韧性十足的蒲苇经捶打多次而柔软。蒲团,柔软也凉爽,又近似席地而坐,好东西。喜欢席地而坐,母亲央人编结了一个。
泡一壶苦菜茶也不错。苦菜长在山野,中医认为它有清热凉血解毒明目之功用。每年夏初,母亲去野地里剜一些苦菜,摘净老叶,洗去泥土,晾去水渍,做成茶备炎炎夏日用。沸水中,苦菜一点点舒开,如出土新芽展开身躯。枯萎的叶一点点变绿,一点点丰满开来,那绿透出来,一丝丝地透出来,如蚕吐丝,那丝又如墨入水渐渐散开来,苦菜完完整整盛开在水中,如诗如画。别家的苦菜茶是碎的,苦菜叶嫩,炒制易碎。母亲有法子。
站起来,打一桶井水,置茶杯于井水中,凉透。茶入口,微苦。入腹,沁凉。
怎样的惬意?寂静得近乎寂寥的日子,一个人沉在这夏日的寂静里,如秋露绽放在草尖,如雪花飘在江心,如种子的嫩芽展开小手去拥抱一个新鲜的世界。。。。。。
(五)
山为门,门里门外两个世界。
夏初,循着如绳的路进山来,一下迈进了另外一个世界,我曾经熟悉的世界。
不知是山高,还是空气清净的缘故,阳光浓烈得如同翻滚的麦浪,滚得漫天漫地,炽热,明亮,纯净。
白花花的世界里,四处皆山,也只有那个形容山多的俗不可耐的词语才最恰当。层层叠叠。山占了这个世界的三分之二。远望去,山间散乱着一些墨点,一个个,如大幅宣纸上随意抖落的墨,一下让这白花花的世界有了生气和重量。
成排的树环着一家,绕着一户,牵连不断就成了小村子。树冠茂盛得如同秋日农家的柴草堆。枝枝桠桠伸展开来,遮盖了院子,一院阴凉。遮盖了村庄,远望去成了一个墨点。
山里的村子都不大,十几户,几十户,就团成了一个村子。老老少少,算起来,也就百十号人,多得也不过三五百人。这些村庄,在如海的苍山中,也不过是一粟,更不用说人了。山里的日子渺小,静悄悄,也旧式得很。
孩子上学去了。大人和牲口下了地。黄狗卧在门洞里,吐着舌头,鲜红。街上只有白花花的阳光在张狂,刺眼,让从村外进来的人禁不住产生错觉,村外的光顺着街道弥漫了过来,又出南街而去。
走在街上,想起父亲总是扛着铁犁,赶着黄牛,出西门,背着一身阳光朝着地里走去。天黑了,黄牛沓沓而行,父亲扛着犁跟在后面,嘴边不时红光一闪,有时也会传来父亲的咳嗽声。旱烟像山里的生活,容不得你不咳嗽,甚至会把人憋得脸发紫。父亲像极了黄牛,疲惫的身影,辛劳的一生,木讷。
这个废弃的院子。算不得屋了,顶已没法遮挡自天而降的雨水雪花了,总算还有几根柃木撑着,几棵草茁壮向着天空成长。门上有一把锁,锈迹斑斑。地上枯枝杂陈,野草青青,空气中弥漫着陈年的腐味和铁锈味。杏树下,不小心踏着一堆枯枝,或者踢翻一页瓦,粉红的潮虫突然四散而去,入了枯枝,入了落叶。密密匝匝的叶子中间,青杏还小。树下有一缸,残破。缸内有水,褐色。说不清是缸的颜色还是水的颜色,红虫如线头,摇摆着上上下下。
没人住的院子,也就没了烟火气,老得也快,就像老人不喜欢楼房一样,老人以为人离不开地气。其实,地更需要人气,没了人气,没了烟火气,也就没了家了。
想着那棵杏树,突然想起一句诗: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六)
母亲终于要离开山里了,在班车的喇叭声和我的催促中。
母亲在山里生活了六十六年。六十六年的日子中,有二十一年是在距我们的村不远处的一个村子里度过的,母亲的这二十一年一如我的童年和青年一样,转眼就过去了。母亲的四十五年时光就在她身后的这个院子里慢慢消磨去的,一天天地消磨,从地里到家里,从家里到地里。先是在生产队里挣工分,后来在自家的责任田里劳作,就这样反反复复地重复着大同小异的每一天,也许说熬过来更确切些,毕竟山里的日子更苦些。等到母亲送走了自己的婆母,抚养大了三个儿子,终于可以闲下来时,她老了,我的父亲也老了并突然去世了,于是她一个人呆在山里,守着这个今天要离开的院子,为我逝去了的父亲守着,也为我们守着。她一直希望我们能早一点退休,回来盖一溜房子,我们兄弟住在一起,和她住在一起,一起守着这所院子。这所院子是爷爷和奶奶给父亲和母亲的礼物,这也是我们家最早最贵重的财产,父亲和母亲在我们兄弟三人相继来到这个院子前,除了一身用于劳作的力气,就是这所遮风挡雨的院子了,艰难的岁月里能有这样一个院子,简直可以说是值得自豪和倍加珍惜的。应该感谢我那未曾谋面的爷爷,他给了我父亲一个家,给了我母亲和我们兄弟三人一个具备了家的基本功能且最牢固的院子。
院子很大,计有正房七间,配房一间半,猪栏两间,更有一圈石头砌成的围墙,院子里和四周有些树。树,一天天长高,一年年长粗,长大了就伐,伐了再栽,也不知栽了多少茬树,四周从来没少了树。这些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是希望,一个可以预计但不可以准确预计的时间里,它们不是现钱,只是希望。父亲曾指着这些树说,这就是供你们上学的银行。父亲不准许我们攀爬,也不准我们随意折些枝条,无论是喂羊还是编个草帽。更不准把牛或羊拴在树上,牛或羊会啃了树皮。牛羊不啃树皮,树也怕天长日久地折腾。父亲总是在西墙下立一个木桩,栓牛或羊,牛羊多了,就多立几个桩。即使直到要告别这个院子的今天,似乎西墙下还有着一根根木桩。父亲走了,牛羊之类的那些生灵也就卖掉了,光溜溜的木桩似乎一直还在,在西墙下。记忆中,父亲总喜欢蹲在地上吸烟,看牛或羊吃草,那盯着牛或羊的眼神很独特,直到今天我才读懂了那眼神:恨不能牛或羊一天就能长大,恨不能那牛毛或羊毛一下子变成缴纳学费或置办物品的钱。
母亲终于要离开山里了。
母亲的身后是一个大院子,五十年里围墙也没多少变化,没加高,也没矮了,风雨霜雪不曾消磨去多少,偶尔掉下一块石头,父亲或母亲总是及时把逃离的石头请回原位,于是这些石头经爷爷的手站在了这里,又得父母看顾着,竟一直站了五十年,结实并忠诚地维护着院子和院子里的一切。
还是有些变化。组成围墙的一块块石头,历经五十年的日月轮回风吹日晒,就像父亲慢慢老去一样,它们似乎黯淡了许多,像极了墙角卧着的一头老牛,少了力量少了虎虎生气。此前并没注意到爬满南瓜秧丝瓜秧甚至长着一些随风倒的青草的石墙会老,一如我不知道父亲何时出现了第一根白发,何时他的腰弯了,也不知道父亲何时竟不吸烟不喝酒了。。。。。。。。不只是石头会老,房子老得更快。爷爷亲手造的草屋,结实的地基,粗大的梁木,只是房顶的草经不住岁月的淘洗,变薄了,有时会漏雨。父亲和母亲就续上新草翻盖一下,继续住。不论怎么翻盖,地基没动,房梁没动。直到村子里满是新瓦房了,父亲召集几个人在草屋上加了层红瓦,也算是瓦房了。只是比不得那些一律高大一律红砖红瓦的房子。父亲还很穷,一些血汗钱陆陆续续在我们开学之初换了主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用血汗换来的钱,不会在父亲手里停留多久,钱来了,马上就走了,似乎总是入不敷出的时候多。迫不得已时,他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兄长去生产队挣工分了,和父亲母亲一起养家糊口,供养着两个弟弟一路读书去。
生活不论多么艰难,孩子的日子总是快乐而又短暂的。日子的苦涩和漫长总是围着父亲和母亲。父亲总是扛着铁犁,赶着黄牛,出西门,背着一身阳光朝着地里走去。天黑了,黄牛沓沓而行,父亲扛着犁跟在后面,嘴边不时红光一闪,有时也会传来父亲的咳嗽声。旱烟如同山里的生活,容不得你不咳嗽,甚至会把人憋得脸发紫。父亲像极了黄牛,疲惫的身影,辛劳的一生,木讷。母亲也总是在父亲走后收拾一下院子,就赶去地里忙碌,又总是在父亲回家前,背着一些青草或柴草赶回家里。做饭,五口人的饭菜,牛也要吃草,鸡鸭也要操心,还有做一些猪的饭食。母亲总是喂一些猪,家里没什么副业,养猪换些钱,父亲的土地也需要大粪支持,店里的化肥对父亲来说总是太贵。
今天,被围墙和两把新锁箍住的院子,在四周高大树木掩映中,在众多年轻人的瓦房中,竟如驼背的老者,矮小,沉默,并从此彻底孤单着。人啊,竟这样经不住老,没怎么感觉中父亲老了,母亲也老了,院子竟也老了。
母亲终于要离开山里了。
母亲站在屋里,看去,似乎一一记住某些物件的位置,又似乎是想把所有装在心中带走。看了这个屋,又去那个屋看。然后,母亲带上门,亲手挂上锁,啪的一声,新锁清脆地告诉母亲这扇门关闭了。
母亲抓起扫帚扫院子,地上留下了细细的纹路,因了院子里的树,和磨盘,还有几个大缸,纹路有些杂乱,一如母亲的心。她不情愿离开,可再也无法拒绝儿孙辈要她离开山里的请求了,母亲的确老了,需要我们去看顾她了。即使在一些可以知道的日子里,母亲并不需要我们看顾,但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需要天天看着她,我们不想为她担心。母亲疼爱自己的儿子,更疼爱儿子的孩子,祖孙感情极佳,竟惹得村里的许多老人羡慕不已。
母亲在中午扫院子,这是不多见的。每天,母亲把鸡赶出院子,就开始扫院子,院子必定要在母亲的手下干净起来,母亲的一天才是真正的开始。毕竟深秋了,扫过去,身后有叶落下来,在刚刚扫过的地面上悄然停留,有枯黄的叶子,更多的是土灰色。母亲矮小,又瘦弱。背着母亲的话会应该很容易。母亲在我记忆中一直瘦弱,用母亲的话说就是吃龙肉也胖不了。今天,看着母亲走来走去,又忙着扫院子,我也只能看着。看着母亲矮小的的背影,禁不住想拥抱一下母亲,想亲近她,想告诉她大家是因了担心她才让她离开山里离开这个院子的。我知道我不能拥抱母亲。记忆中我和母亲最亲近的一次是母亲给我烫脚。那一年我四十岁,脚伤了,母亲采来山里的草药用水熬了,端在我面前。我坐着,母亲蹲着。母亲用毛巾蘸了热水,在我的脚腕上热敷一阵,再用手不断按摩脚腕。母亲用手按摩着我的脚腕,我看着母亲花白的头发,禁不住五味杂陈。这竟是记忆中离母亲最近的方式。我是母亲的儿子,我吃了母亲的奶水长大,可我不记得我趴在母亲怀抱里吮吸奶水的时候了,也不记得母亲牵着我手送我去报名上学的时候了。母亲从来不说拉扯我们三个长大的难处,也不说我们小时候的事,但应该有这些,只是我没记住。我也没握过母亲的手,更不用说给母亲洗脚了。即使想给母亲洗脚,母亲也不会同意。母亲是个旧式的女人,她不会习惯的,自然更不会习惯拥抱,我们是她的儿子也不会习惯这些。
母亲矮小的身影,干净的地面,还有格外醒目的落叶,散落在母亲即将要离开的院子里。一阵凉意袭过,禁不住心生悲凉,这多像人的一生啊,不停地朝前走着,不知不觉中就老了,回头一看,身后总是弯曲的身影,弯曲的道路,路上还有一些落叶飞雪。。。。。。。
母亲要离开山里了,这是母亲第一次要长久远离这个村子这个院子,母亲这六十六年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去山外的小城看看自己的孙辈。四十五年的日子里,她就从这个院子走到地里去,从地里走回这个院子,母亲几乎没离开过这个院子。母亲回娘家也当天回来,两个村子相隔三里地,即使和父亲吵了架回娘家去了,也当天回来。母亲是个要强的人,在我四十多年的生命里,我见证着母亲的沉默和刚强。也见证着母亲的善良,母亲从没打骂过自己的孩子,甚至从没一句恶语相加,也没和任何乡人吵过架。
今天母亲要离开山里,离开这个村子,离开这个守了大半辈子的院子。
母亲要离开山里了。
母亲在迈出大门口的刹那,回头,啪的一声带上门,门环当啷一声,我仿佛听见母亲的心哭了,母亲要去一个她全然陌生的环境。
母亲要离开山里了。
母亲坐上车了,车穿村而过,院子在身后了,村子也要在身后了,母亲不会挥挥手,也不会在心里说声再见,母亲不会这样,她只是握着我的手,不知何时母亲竟攥着我的手了,这是母亲第一次握着我的手,也是我第一次握着母亲的手,这年母亲六十六岁,我四十二岁,是我们要离开山里离开我们的家的2009年x月28日的中午。
母亲要离开山里了,我们也就彻底离开了山里。这二十多年里,先是我离开了山里,出去读书,又在小城里安了家。弟弟也离开了山里,前些年又去了成都。再后来那个在生产队里练了一身种地本事的兄长也离开了山里,在小城里安了家。山里只有我们的父母亲和院子了。后来父亲走了,山里就剩下母亲和院子在。而今,母亲也老了,也要离开山里了。老辈人说,娘在的地方就是家。在今天之前,母亲的家是我们的家,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家就是母亲的家了。
母亲离开了山里,身后是一个村子和一个院子。这个院子有几间屋,有些树,还有一圈围墙,今天又添了几把新锁。
几把新锁,锁住了屋门院门,也锁住了三代人曾经在这里的生活,爷爷在这里住了十几年,父亲在这里住了一辈子,我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年。
母亲离开山里了,身后是上了新锁的一座院子,钥匙正攥在母亲手里,钥匙将陪伴着母亲去小城了,我知道故乡正远去,我那把打开故乡的钥匙从今天起就丢了,丢在了这风里。纵使我带着钥匙回到山里,将怎样面对这个空无一人的院子,怎样面对这渐渐衰老的锁,它今天闪着灰色漆的光,不久也会老去,甚至比想象要快得多,锈了,让你空有一把并没褪色的钥匙。还没完全离开,我就见到了这样的一幅画面:大门上锁已锈了,院子里空荡荡的,屋已算不得屋了,屋顶已没法遮挡自天而降的雨水雪花了,总算还有几根柃木撑着,瓦上有些草茁壮向着天空成长或枯萎。地上枯枝杂陈,野草青青,空气中弥漫着陈年的腐味和铁锈味。不小心踏着一堆枯枝,或者踢翻一页瓦,粉红的潮虫突然四散而去,入了枯枝下,进了落叶中。树下的缸也会有些水,褐色,说不清是缸的颜色还是水的颜色,红虫如线头,摇摆着上上下下。
院子没了烟火气,老得也快。老人说住楼房人就离开了地气,离开了地气人就更容易老。其实,地也需要人气。一个院子除了自然的风声和或绿或黄或秃的枝干,没了人气,没了烟火气,也就算不得家了。
唯愿记忆不老。
母亲要离开山里了。在一个深秋的中午,母亲跟着她的儿子离开了生活了六十六年的山里,班车上满是人,有老人,有青年,吸着烟,一脸无所谓;也有孩子,孩子笑着顽皮着出山了,
母亲终于离开山里了,她攥着一串钥匙,攥着我的手离开了山里。群山在身后了,那个叫常岭的村子在身后了,常岭村里那个从此闭锁的院子也在身后了,还有村子不远处的一个坟场,父亲在那里安息,在那里安息,我在不远处挣扎,挣扎呢,您看着,您看着。。。。。。
(七)
喜欢夜空,尤其是山村的夜空,纯净,真实,黑就是黑,一点也不虚假,让星星闪烁起来,让天地空旷起来。
院子里,或村头,仰望中,繁星闪烁中有童年的一切。祖母的牛郎织女传说全然不同于文学中的任何一个版本,它属于祖母甚或曾祖母的,估计曾祖母也给我父辈讲过,口口相传,絮絮叨叨在夜空下。说牛郎织女,就骂王母娘娘心硬。说着雷锋塔下的白蛇,就责骂和尚多管闲事。说孟姜女哭长城就骂修长城的人,她不知道秦始皇,也不知道秦代,总是说从前有一年。祖母是虔诚的佛教徒,骂王母娘娘骂法海骂皇帝,像骂邻居家那个喜欢偷鸡摸狗的二流子一般,也顾不得什么神仙和佛了。也说些不孝子孙不得好报的故事,老年人总喜欢讲一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故事,借鬼神的力量在孩童幼小的心上埋下向善的种子。寒门更怕出逆子。
祖母是一个很好的人,她去世时,不知道有没有流星划过,大家只是一起哭她,乡人和我们一起流泪一起埋葬了她和她的故事。
流星划过,如箭劈开黑夜,飞逝。祖母说,那是人间一个好人去了。这句话影响我好多年。和女儿一起看流星划过,也告诉她,人间一个好人去了。女儿反驳说,那是流星,与人死无关。读着《十万个为什么》看着《发现和探索》长大的孩子,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物质丰盛,和科学带来的理性,他们喜欢用个性和科学去解释一切。
有个乡村可以怀念,有个乡村院落可以驻足,可以安卧,该是幸福的人。
院子外的世界是山,庄稼,野草,河流,锄禾日当午的农家人。满山牧羊的老汉,山里没闲人。
山里的生活其实很苦,自耕自收的日子不容易打发。靠天和汗水吃饭的山里日子长,庄家总是长得那样慢,一场雨总是等着盼着也下不来,山路上的小车总是吱吱嘎嘎地走。。。。。
山里的日子苦,可也素净。
山多,树木多,野草多,人不太多;山里声也多,风过树枝的声,挤进门缝的音,鸟鸣叫,虫吟唱,牛羊轻唤之声,这里有一声,那里又一声,天上划过一串婉转,地上飘来三两声低沉,算不得此起彼伏,也交错着,充盈着耳畔,让你产生时光停滞的错觉。
因了城里的一份工作,不用挥汗如雨或起早贪黑地熬。也因了山里有一处院子可以驻足。得以享受山里的素净。享受这份惬意也不容易,常常伴随着一份自责,路不够宽敞,山外的蜜桃两块六一公斤,这里一块六七一公斤。修路谈何容易?父老乡亲天天咀嚼那苦涩的日子,几只羊羔的降生会让老汉在寒冬里蹲守一夜,陪伴他的除了冷夜就是一烟锅子又一烟锅子的烟丝。劳累了一天,路上,风卷来的枯枝,谁落下的一把草,拿回家顺手丢在墙角或炉子里。丢在墙角的草,也许不久就烂了,烂了也是肥料。
深知稼穑之苦,却还是说着山里的好。用母亲的话说就是:饿你三天,就不说山里好了。其实,母亲也说山里好,在山里自在。劳动了一辈子的母亲不怕苦,怕城里的憋屈,住在楼里,邻居也不串门,守着电视没人说话。
山里,流星划过,就是一个人消失了的地方,在女儿眼中,那是陨石燃烧了,与曾祖母的童话无关。
(八)
这一年的冬天有些冷,冷得让我穿上了多年不穿的厚棉袄,是的,是棉袄,不是羽绒服。穿棉袄,起初是我顺手从记忆里掏出来的,也巧,就在一个我不太熟悉的柜橱里掏出来了,穿上了,让我想起了娘。
娘,给我棉袄的人,在一个冬日。那个冬日比这些年来的冬日更冷,天冷,风冷,地冷,路也冷。
那一日,自然是冬日,进山的前一日,因了我不可预期的第二天让我记住了那一日。那天,我忤逆了,不上学了,所有人都没说话,所有人是指父亲和母亲,还有哥哥,也有小弟,那时,弟弟还不在所有人中,他还小呢。
忤逆的后果并不可怕,接过了父亲递给我的扁担绳索和一把斧头就进山了。看看斧头,满锋利的,照着初升的阳光,贼亮贼亮的,斧柄也长,握着足以到我胳膊肘,要是插在腰上,估计爬山也让腿弯有些负担。索性,也就是索性,我扛着绾着绳索的扁担,提着贼亮的斧头进山了,我知道这是忤逆父亲的代价。
忤逆产生的力量很大,大得不计后果。
风从山里吹来,迎面劲吹,吹着脸,吹着棉袄,钻进领子里袖子里,有风又从裤腿里钻上来,合在一处,遍体生凉。无论我怎么跑,都感觉不到一点暖意,除了双腿感觉累。
进山的路窄,也如蛇形的踪迹弯曲,阳光在头顶上,算是有些大意吧,只是风冷了些,从四面八方吹来,围着我吹,追着我吹,从离开家时,从出村子时。走过哑巴岭时,前方吹来山风,大且硬朗得如扁担,粗糙的扁担,于是我全身发紧,紧得腿肚子有些硬,脚步也有些慢,一直紧到我放下扁担挥起斧头肆无忌惮地砍着树木,所谓的树木也只是小孩子胳膊粗的树,这样的树不用去树头,也不用从地平面砍,只是顺手一挥,齐腰而断,再一挥斧头,树头也去了,大半人高的树干再一分二,恰恰容易捆扎,也容易挑下山去。
回家的路正如进山的路一样长,扁担绳索斧头外,多了些柴草。挑着担子提着斧子走出大山时,夕阳在山,寒风又吹起来了,从四面八方吹来,围着我吹,追着我吹,除了给我一些冷,还让我的脚步更加歪歪斜斜地走,毕竟肩上有个担子。
走,硬着头皮走。走不动时也要走。进山时我可以不走,不走我就停留在离开村子不远处的寒风里,村子不远处的寒风毕竟因了我和村子的关系并不生硬对待我。必须走,挑着担子走,似乎没法出汗,汗在心里就被四周的风抽走了,剩下挥动着的斧头和担子在夕阳里一步步下山来。
下山来。哑巴岭。
哑巴岭,有一个石泉,石泉的水据说不能喝,喝了会哑巴,老人都这样说。我不想喝水,只是累。担子,越走越沉。棉袄,也越走越沉。一心往前走,两条腿罢工了,于是跌坐在地,哇哇大哭……
哭完了,暮色也上来了,还得走,来路一如线,孤单着,绵长着,沿哑巴岭而下,沿着小河而去,小河拐弯的地方是小路拐弯的地方,我的小路的终点就在小村的东南一个小院处。
一步步走,一步步挪。夜色拥抱我和我的担子了,剩下我挥动的斧头在黑暗里明晃晃了,其实这明晃晃只在我手上和心里。
村子在我迈入第一只脚时有了灯光,灯光如豆,星星点点。星星点点中,我知道栓住吃了饭在做作业,明存正捧着收音机听杨家将呢,还有英子呢,英子也许在刷碗,也许在提着水桶喂猪,她家里养了三只猪,猪栏在核桃园里。英子挑着担子,一头是装着猪食的水桶,一头是一个筐,框里放着一块石头。英子挑着担子走,手里挥动着大马勺,似乎驱赶着什么,一如我挥动着明晃晃的斧头。
他们都在灯下,英子在去核桃园或从核桃园回家的路上,我没看见,他们也没看到我挑着担子提着斧头,踉踉跄跄地进村来,多年后,我怕踉踉跄跄这个词语,这个词语除了形容有些喝了酒的人的脚步外,就是形容那一日我进村的情形了。
踉踉跄跄,确实是踉踉跄跄中我把斧头插进了我面前的柴堆中。
近了,院门外有人站立着,是父亲。父亲看我来了,转身进了院子。扔下担子,我也进了院子,径直进了屋,上了床,夜色关在眼睛的外面了。
那一日,太冷。寒气一直潜伏在我身体深处,疯到特别冷的冬天,他就钻出来让我知道:风从四面吹来,劲吹,吹着脸,吹着背,吹着棉袄,钻进领子里袖子里,有风又从裤腿里钻上来,合在一处,遍体生凉。
我的棉袄!我的山路。一直走着的山路。
(九)
吃了几杯酒,天也就暗了,酒劲也上来了,免不得困乏,索性和衣半躺半倚在座上。
人,有时拿困乏毫无办法。头一挨着枕,眼皮麻得发涩,精神却异常活跃,仿佛身心分离了,也恼不得。
周围一片静默,那些老器物更暗淡,也更泰然了,一如我的父老,早饭或午饭后,找个寂寂处,借一堵矮墙的阳光,不管地上土墙上灰,斜斜倚着,眯着眼,禅定般,任凭时光走自己的路。
静默中,听得浅浅地吟唱,是秋虫,分明与夏日无二。虫对季节的变化比人来得敏感,要不,有个节气叫惊蛰呢。秋虫的叫声,一阵紧,四处皆是,声声入寂寥之耳,便觉心空荡荡得,无所依。一阵稀,声息全无,令人无端提起心,等着那一阵紧起,鸣叫反反复复,心也忽上忽下的……
静默中,总躲不开声声吟唱,意识里便多了些门外的东西。
毕竟是秋夜了,月光清亮亮的,地上有或浓或淡的影,树的,房子的,围墙的,还有那盘石磨的,影似乎无所不在,倒是清亮亮的月光少了些。月光只到门前,走不进屋子,即使这是一间乡间老屋也不行,明晃晃的灯光遮掩了月光的身影,无影可成。
门外,秋日了。
这秋夜的困乏实在有些无聊,小时候,玩累了,倒下便睡,何曾翻来覆去?秋夜的乡村更像儿时的乡村,今夜,月依旧,院子依旧,一些人老了;有些人更老了,老成了一段故事。
乡村秋夜,月光无处不在,影像无处不在;暗夜里,黑漆漆的村子,黑黝黝的静默。山里的夜,有月或无,于时光无所谓,夜深了,家家入了梦,或长或短的鼾声,只有秋虫知道了,或者还有守夜的犬,和咀嚼着草料的黄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