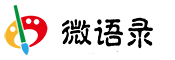2014年诗学笔记
西渡
126.诗人们认为想象是继信念而来的最伟大的力量:在位的君王。但正如信念不可独自为王,想象也不可独自为王。信念为王产生十字军,想象为王也会产生奥斯维辛和古拉格。无论在政治的秩序里还是在诗歌的秩序里,理性都不可或缺。
127.我们不能用定义的网把所有的诗打捞到岸上来。无论多么完美的定义,漏网之鱼总是比网中的鱼多。因为诗,比我们所有的网广阔。
128.艾略特给诗下过一个最宽泛的定义:诗是自古以来一切诗所构成的有机的整体。这是正确的定义,却是毫无意义的定义,因为它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关于诗的知识。臧棣的定义——诗的定义在未来——虽然也没有给我们提供关于诗的现成的知识,却是启示性的。普通读者对于这样的定义会感到同样的不满足,它却对诗人构成了重要的启示。
129..斯蒂文斯说,我们从未困惑于认出诗歌。这只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经验丰富的读者自信他能从一行诗判断一首诗的好坏,或者仅凭一本诗集的标题评估一个诗人的潜质。这当然有其心理和实践上的依据。但是不要忘记,人们认出陶渊明花了千年,认出杜甫也花了数百年;即使在《唐诗三百首》这样的选集中也存在鱼目混珠的情况。诗比所有的定义的网广阔,也比所有的读者广阔。
130.斯蒂文斯说诗是诗人人格的一个过程,不可能有无关诗人人格的诗歌。然而,他又引亚里斯多德的语录说,诗人要尽可能少地表现自己的人格。艾略特也说,诗是逃避个性。这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实际上却是逻辑地统一的。因为“头脑的主要特点使不断地描述它自身”,“诗人的头脑在他的诗篇里不断描述它自身就像雕塑家的头脑在他的形式里描述它自身,或者像塞尚的头脑在他的‘心理学风景’中描述它自身”。诗人永远不用担心失去自我,如果他拥有一个自我的话。诗人需要担心的是他一直在谈论自我中毫无价值的部分,某种敝帚自珍的“艺术家气质”。真正的自我归根结底是那个属于全人类的“整体人格”的体现,是那个不可知的自我,也就是那个我们不能认识却能感觉到的真理。瓦莱里说,“凡仅对我们自身有价值的就是没有价值的”,这就是文学的定律。
131.瑞恰慈说,柯勒律治最光辉的成就之一就是指出了“意识到一种音乐的快感是想象的赐予”。音乐在诗中是一种组织的力量,是是它把纷乱的、互不联系的各种冲动组织成一个单一的、有调理的反应。一首诗如果缺少音乐性,就意味着诗中的各种冲动仍然是未加组织的和混乱的,也就意味着诗的失败。
132.叶芝说,必须从严肃的诗歌中清除那种像奔跑的人那样的强韵律,因为后者的产生,是意志仅仅着眼于做或不做某事时说造成的结果;应该去寻求那些震颤不定的、沉思冥想的、有机的节奏,这些节奏体现了想象,它既无所向往,又不会有所仇恨,因为它已经和时间断绝了关系,唯独希望放眼观看某种现实、某种美。叶芝的上述观点当然关联于他所钟爱的某种风格,但仍具有普遍的意义。理解叶芝的这番话,你大致会对诗歌的音乐性形成比较正确的观念。
133.帕斯说,音乐是诗的一个危险的同盟。确实如此,如果把音乐性理解为音乐的音乐性,而不是诗的音乐性。这个危险的同盟在一千年内几乎窒息了中国诗歌。
134.有一种诗歌的音乐性是献给聋子的耳朵的——像贝多芬一样精通音乐的聋子耳朵。无论多么完美的嗓子也无法传达这种音乐性内在的丰富、细腻和万千变化。在这种音乐性的领域内,仅仅一个词语就包含了丰富的和声,仅仅一行诗就呈现了丰富的动机。
135.希内说:“诗人说话的音调的核心与其诗歌的音调的核心之间,他的原始音调与他所发现的风格之间具有某种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是对的。但诗人个性化的声音既非全然建基于某种“自发的敏感”,也非全然来自他听到的其他诗人的声音(所谓“所流出的便是所流进的”),而是建基于诗人有意识的风格化的努力。诗人的声音归根结底是一种创造。如果我们在一个诗人的作品中总是听到他日常生活中说话的音调,就会干扰我们对其诗作的欣赏,也说明诗人还没有创造出他自己的个性。诗人说话的音调是他发展其个性的胚芽,但这是一个未加工、初始的胚芽,要发展成为真正的个性,诗人还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136.为了研究诗的韵律,庞德希望将词语与节奏分离,以免文字的含义分散诗人对节奏的注意,所以庞德建议初学者研究异国语言的韵律。但庞德的意图不会成功。词语的声音与意义是一个连体儿,试图将它们分离的努力,将会同时伤害两者。在这一点上,曼德尔施塔姆的看法更为内行,“词的有意识的含义和逻各斯都是一种极好的形式”。也就是说,诗人必须把词的声音、意义、书写法和诗的组织一同视为词的质料的不可分割的性质,而加以同时性地研究和把握。这一历程从马拉美的时代已经开始了。瓦莱里说马拉美“以非凡的成就论证了诗歌须赋予字义、字音甚至字形以同等价值,……内容亦不再是形式的起因,而是效果之一种。每句诗都成为一个实体,它有自己存在的物质原因。”因此,瓦莱里说:“对别人来说是形式的,对我来说是内容”;贝恩说:“艺术尝试着在内容的普遍颓败之中,把自身当作内容来体验”,“形式就是存在,是艺术家的目的,艺术家存在的任务”;埃米尔·施泰格说:“形式是最高的内容。”
137.庞德身上还保留了根深蒂固的分析的习惯,他不止割裂声音与意义,还试图割裂感觉,他的告诫“不要用一种感官的知觉去解释另一种感官的知觉”对诗人是有害的。诗人的首要目标是身心的合一和各种感觉的合一。帕斯说:“阅读一首诗是用我们的眼睛倾听这首诗。倾听一首诗是用我们的耳朵看这首诗。”人的感觉本来就是综合的,颜色里有芳香,声音里有形象,思想里有感情,感觉中隐藏着思维的运动。分析的习惯不是庞德一个人的恶习,也是大多数英美诗人的恶习。庞德的目的是精确的表现,但综合的表现并不就是含混,它是更高的精确。
138.瓦莱里说,如果你写诗是从思想开始,那就是从散文开始。诗中的思想是思想的一种特殊形态,它是“不能写进散文的思想”。
139.诗凭着听力认出世界,散文则是凭着气味闻出世界。声音是精神的,气味则属于身体。
140.蒙塔莱说,任何诗的发现都孕育于散文的土壤。然而,从散文的土壤中恐怕只能孕育出散文。在一个人身上,诗的才能的发展快于散文的能力。一个人可能要到三十岁才能写出有价值的散文,然而,一个诗人到二十五岁就已经相当成熟了。可见,诗的才能是独立于散文的能力而发展的。有的诗人写不了散文,正如有的歌唱家是结巴。好的小说家同时写一手好诗的则是个例。
罗伯特·洛威尔认为,在表现真实的经验上,散文家比诗人更有优势。诗的形式加工会使最后呈现的东西失去现场感。他认为在这点上,现代诗人中只有弗罗斯特是成功的,艾略特的《荒原》也只有部分的成功,而弗罗斯特“既具备了照片的真实,也具备了艺术的手腕”。但是,我敢保证,人们记住的诗句要比小说的细节更多。诗当然有它所不擅长表现的东西,但是你很难说诗比小说更少真实性,除非你把真实性限定在小说所擅长的经验上。“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有多少细节的真实和心灵的真实!对我来说,它胜过一部小说。
141.诗的重要性见于它的复合性,它所唤醒不是某种单一的感官知觉,而是我们的全部身心。诗由此极大地扩展了我们的潜力,并把我们还原为一个完全的人。这一点在一个分析的时代尤显珍贵。瓦莱里说,在读小说的时候,读者仅仅是一个脑子,而诗动用了读者的全部身心。
142.真正的诗人依靠耳朵判断诗歌的音乐,而诗律学和不合格的读者依靠计数。新月的失败在于向计数主义的妥协。就此而言,新月派中只有徐志摩没有丢弃诗人的直觉。
143.艾略特说诗人应该像闻到玫瑰花香一样闻到他的思想;叶芝说诗中的思想应该像一个女人献身于她的情人一样献身于某种情感;瓦莱里说思想必须隐于诗中,一如养分隐于水果之中。诗人的思想不是出自他的头脑,而是出自他的血液、汗液和精液。诗中的思想就是行动的诗人。
144.现代汉语使思想进入诗歌成为了可能,但前提是诗人要先有思想。帕斯说缺少哲学和宗教的体系,缺少意念和信仰的一致性在威廉斯的诗中造成了一个空白,那也是当代美国文化本身的空白。遗憾的是,对我们而言,那不是当代文化的空白,而是源于文明本身的空白。思的诗在我们这里几乎还不曾出现。
145.帕斯捷尔纳克认为莎士比亚的无韵诗是“最高级诗歌的最佳范例”,因为“在这种诗中,不强调,也不突出韵律”,它“永远渗透着散文所具有的朴实与清新”。这是对诗歌韵律以及诗与散文关系的最明澈的见解。可惜它永远不被韵律家所理解。
146.奥登说,诗和散文之间的区别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要为这种不同下一个定义纯粹是浪费时间。问题是从来没有纯粹的诗和散文,“言语不会变成音乐,它也不会变成代数”。
147.庞德说:“要写出好诗,就至少要写得优秀散文一样好。”艾略特说:“诗人如果不掌握散文体就写不出层次丰富的作品。”曼德尔斯塔姆说:“诗歌需要散文,由于没有散文,诗歌已经丧失了空间。”帕斯捷尔纳克说,“诗与散文的交替是莎士比亚戏剧的主要特征”,并且构成了它最广泛、隐蔽的节奏。诗人们说的是一个意思。
148.瓦莱里说,纯诗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目标。沃伦说:“至少应该尽力把一首诗写得纯净澄澈。”诗人们经常徘徊于把一首诗写得纯净澄澈的愿望,和容纳更多的生活真实的愿望之间。纯诗之纯在雪莱、爱伦·坡、瓦莱里、沃伦那里意味着剔除一切超过必要的杂质,是“尽可能剔除某种可能与其原动力相冲突或者限制其原动力的元素,以尽量求得纯净。换言之,全部纯诗作品,都要求形成一个整体”。乔治·摩尔认为,纯诗是“诗人在自己人格之外所创造的某种东西”。纯诗之纯并不在于与生活相比,它是纯的,而是与自身内在的要求相比,没有超过必要的杂质。“必要”的界限在一首诗的内部,而不在它的外部。一首吟风弄月的诗最有可能是不纯的。因为就其原动力的缺乏而言,它根本没有写作的必要。
149.关于纯诗,波特尔指出了另一种思路。他说:“诗歌不应该比诗人意图的要求更加纯粹。”因此,一首诗可以包含大量乏味的话语,或者传达消息的报道,以便缓解知觉的过分紧张,以利于在“强烈的经验”到来时起到更好的衬托作用。语言都具有某种使我们意识到作为经验的经验、指示经验的本质的功能。就此而言,也可以说,人类一切话语都是程度不等的诗歌。
150.苏珊·朗格说,凡好诗必为纯诗。整个诗的“纯化”问题是一个伪问题,它的产生是由于误解了什么是诗歌,也由于错把某些效果显著的和大多数普遍使用的手法当作诗歌的基本原则,又把“纯诗”仅仅看作用那些手法写成的诗歌。在苏珊看来,什么样的语言是诗的,要靠诗歌内在的意图而定。诗人以诗的原则而运用语言,就可以把律师的行话转化为地道的“诗歌措辞”。苏姗认为,诗歌与实际话语的区别不是程度的而是根本的。诗歌不是真正的话语,不是语言的一种功用,而是以非推理性语言所进行的虚幻的经验或虚幻的往事的创造;“诗歌语言”是对这一目的特别有用的语言。虚幻的往事的创造是贯穿整个文学的原则:作诗的原则。以此衡量,散文也是诗歌形式之一,其功能是创造性的。苏珊反对波特尔把诗歌等同于话语,强调两者之间存在根本的区别,反过来又认为散文是诗歌形式之一。这正是逻辑语言的悖论。凭借这样的逻辑语言,我们永远不能完全地认识诗歌。
151.小诗人比大诗人更纯。纯的愿望是一种心灵的界限感。
152.纯诗在我们这里总让人想起风花雪月。但据瓦莱里的愿意,所谓纯诗指的是一种艺术效果,在其中体现了一种与纯实践世界俨然不同的关系世界,其中的每一词语彷佛都摆脱了其物质属性,纯然指涉自身,而在我们的心灵中引起一种纯粹的感动。就其不与纯实践世界相涉之点而言,与这一效果最为接近的是梦。风花雪月本身不能达成这一效果,尤其当它们成为某种特殊情调的固定符号的时候。关键是纯诗依赖于一种创造的行为,它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感动我们的新的关系,而风花雪月的诗意依赖于一种题材的重复。在这一点上,它与纯诗毫无关系。同理,梦的重复也在这一点上显示了自己的不纯。
153.就纯粹的程度而言,诗永远无法与音乐相比,甚至也无法与绘画相比。语言在其最纯粹的时刻,也仍然保留了指涉实践世界的可能和意向。但恰恰是诗为我们的精神世界中那种最纯粹的时刻提供了命名。这一事实难道不发人深省吗?只有诗激发了我们最全面、最深刻的身心的激动。在诗歌的体验中,不仅我们的身体,也不仅我们的心灵参与了那种内在的激动,甚至与这一激动格格不入的头脑也参与并陶醉其中。头脑或曰理性在诗歌体验中不仅有其贡献,而且在这一体验中实现了奇特的变形——它自身变成了诗歌魔术的一部分。早在戏剧之前,诗歌早已经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形象、声音、意义、身体、心灵、理性同时服务于一个目标:从物质向梦幻的变形。用康德的话说,“如果我们把美的艺术的价值按照它们给内心造成的教养来估量,并采取那些为了认识而必须在判断力中集中起来的能力的扩展作为尺度”,“诗在一切美的艺术中保持着至高无上的等级”,而音乐“在美的艺术中占有最低的位置”。
154.诗永远是一种间接性的艺术,它首先诉诸我们的理性,而并不直接挑动和刺激我们的感官。当诗人们大谈诗的直接性的时候,有必要提醒他们语言符号首先是一种概念。在一首歌中,间接性的歌词(诗,如果它曾经是诗)被转变成了直接性的音乐,然而,与此同时,作为诗的一切优越性也就同时失去了。
155.瑞恰慈说,容易受讽刺的诗不是最高级的诗,最高级的诗的特点总是讽刺的。讽刺的意思是引进对立的、补充的冲动。容易受讽刺的诗中的冲动组合是由平行的、同一方向的几组冲动构成的,而在讽刺的诗中,凡是辨认得出来的冲动都特别驳杂,不仅驳杂,而且互相对立。
【西渡简介】
西渡,诗人、诗歌批评家。北京大学文学学士、清华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研究员、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1967年生于浙江省浦江县。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并开始写诗。1990年代以后兼事诗歌批评。著有诗集《雪景中的柏拉图》(1998)《草之家》(2002)《连心锁》(2005)《鸟语林》(2010),诗论集《守望与倾听》(2000)《灵魂的未来》(2009),诗歌批评专著《壮烈风景——骆一禾论、骆一禾海子比较论》(2012)。部分作品译成法文,结集为《风和芦苇之歌》(法国Éditions Fédérop,2008)。其他编著作品有《北大诗选》(与臧棣合编)《戈麦诗全编》《先锋诗歌档案》《访问中国诗歌》《经典阅读书系·名家课堂》《骆一禾的诗》《戈麦的诗》等。曾获刘丽安诗歌奖、《十月》文学奖、东荡子诗歌奖等。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