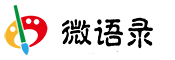✦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蒋硕
中国文体四分法先驱:论晁德蒞译介中国散文与文体风格
摘要:晚清上海徐家汇天主教神父晁德蒞编译的拉丁文5卷本《中国文化教程》是一部供来华传教士学习中文与中国文化的课本,也是一套中国古代经典的文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对当时来华传教士和欧洲汉学界均产生了影响。该书第四卷是20世纪前中国散文最大规模的西译,译者集中翻译中国散文得益于他对中国文体的精准把握和创造性认知。晁氏结合西方文类学,将中国文体大体划分为包括经典圣书在内的5大类,是现代学术中国文体四分法的先驱,亦为西方文类三分法提供了有益参照。一般认为,中国文体四分法晚至民国时期才由中国学人讨论确定,但是晁氏的著述将这一探讨提早至晚清。他的成果对中国文体学、文学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晁德蒞;文体四分法;中国散文译介;《中国文化教程》
作者简介:蒋硕,博士,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中外关系史。
源自:《中国比较文学》2022年第1期,推送获期刊授权。
晚清耶稣会重返江南,将总部设立于上海徐家汇地区。上海意大利耶稣会士晁德蒞(Angelo Zottoli, 1826-1902)用拉丁文翻译了大量中国文献,收录在他的5卷本《中国文化教程》(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下文简称《教程》)中。该书甫一出版便荣获儒莲汉学奖,对来华传教士与西方汉学界均有较大影响。《教程》第4卷供第4年高级班学员使用,编译目的是在前3册中国语言与文化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中文的文体修辞进行训练。本卷内容主要包括散文文体,选文有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楚辞》《庄子》,以及从汉代至明代的“古文”。随后,晁氏又选译了50类古今简牍,并附有用于公函写作的实用资料。由于应用文简牍也大体是由散文写成,所以,本卷全册可说是对散文文体的集中译介。目前,学界在使用文体这一概念时,含义有所不同,这种差异体现了文体概念在中国语境下存在古与今和中与外的差别,在中西比较视野下使用文体概念时,尤其需要区别中西概念内涵的差异。大体上讲,国内对于中国文体学的文体概念更加接近于西方的文类(genre)概念,而西方的文体或文体学(style或stylistics)含义更确切的是指风格或者风格学,亦即是探讨每一种文类特征的学问。为了行文方便,本文仍然使用文体这一国内学界通用的名称,但是本文所说的文体含义属于西方的文类范畴,在个别地方为了不产生歧义使用了文类这一名称,本文中的文体与文类概念含义相同。
✦
一
中国散文小史与文体分类译介
晁德蒞在本卷卷首的序言中讨论了中国散文的发展小史,晁氏所论述的中国散文是与诗歌相对应的包含广泛的文类。它包括春秋三传这类对《春秋》经的评传、《国语》《国策》等史书,也包括老庄、荀子、杨雄、王通(文中子)等儒家、道家的论理著作。此外,晁氏将《史记》《汉书》以降的历代官修正史全部视为重要的散文写作。之后,晁氏重点介绍了唐宋八大家,即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和王安石,认为他们是中国中古散文的主要代表。晁文介绍了八家的籍贯、姓名字号、生卒年、官职、文集名称、卷数和各自的文风,晁氏认为韩愈的风格“雄浑、流畅”(copiose fluente stylo exarata)、柳宗元“果敢而又忧郁”(reliquit nervosa gravique stylo)、欧阳修“和气而又从容不迫”(reliquit leni at presso stylo)、苏洵“渊深多变”(profundo insolitoque stylo)、苏轼“宏肆”(largifluo stylo)、苏辙“深意而从容”(significante pressoque stylo)、曾巩“简洁丰满”(reliquit stylo concise at pleno),以及王安石“清新深刻”(rorido profundoque stylo)(Zottoli 1880b: vi-vii)。(1)晁氏的散文小史明显是按桐城派古文观念进行梳理,几乎未提及骈文家,这篇小史充分体现出了桐城古文的儒家道统观和注重史传的特点。
在这篇小史中,晁氏对宋代以后散文的发展没有进一步说明,在他看来,虽然中国散文的发展此后仍连续不坠,但是新的文体已经兴起。晁序接下来写到中国学童在幼年诵记四书五经之后,会进行“开笔”,主要内容是进行严格的古文写作训练。因此,《教程》在本卷分级教材中为学习者安排了应用书信文体的学习,并认为这好像枝干(ramus)一样,可以作为补充。本卷最后晁氏介绍了“典故”,他认为学习典故十分必要,尤其是对演讲和文体的雄辩方面很有助益。由此,可以看出《教程》结构安排的重要考量是中文语言学习的合理步骤,晁氏根据中文教学法的合理学习阶段进行全书的编排。在第三卷前言中,我们已经了解到晁德蒞学习、参考了清代唐彪的中文教学法著作《读书作文谱》(2),在本卷前言中我们看到晁氏对当时江南学校中幼童学习中文语言文化的方法进行了细致的调查。
《教程》第五卷主要以诗词和八股文翻译为主,但是晁氏在该卷前言中几乎未提诗词问题,而是集中对中国散文的文类做了重点介绍。如果说卷四前言是对中国散文所做的历时性概述,那么卷五前言则是对中国散文的共时性分类,即辨体加以介绍。晁氏说中国散文的文体形式多种多样,每种均由不同名称命名。他将中国文体按照功能不同分为5大类:第一类是出自君主的文书(regio scripto),包括命,令,敕或勅,诰,诏,玺书,札,制,国书,教,盟与誓,铁券文,誓,露布,檄,符,论,赦文或德音文。第二类为上奏君主或朝廷的文书(supplici ad imperatorem libello),包括上书,奏,疏或奏疏,议,封事,启,奏启,剳子或奏剳,状或奏状,对或奏对,题本,奏本,章,表(包括贺表、谢表、近书表、让官表等),笏记,弹事,箴,连珠,牋或箋,书,册。第三类是民事函件(civilibus epistolis),包含公移,状,辞,刺,移,剳,由状,公牒,贴,照会,剳付,案验,故牒,呈,申,案呈,资呈,牒呈,资、牒、关、揭帖。第四类为著述或科举考试的训练(litterariis aut examinis exercitationibus),其中,策包括制策、试策、进策、对策或策问;论包括经论、史论、文论、政论;说包括说和说书,还有原,义,解或释,议,辩,状,简,启,书,志,记,纪事,传,杂著,问对,七(七命、七发),序,小序,引,题,跋,题词,书某或读某,判,批,评,颂,赞(包括杂赞、哀赞、史赞),约,规,戒,文,骈体,楚辞,铭,碑文。第五类有关丧葬事宜(funereis rebus),包括祭文,谕祭文,吊文,诔,哀文,哀策,墓志,行状,墓志铭,权厝志,续志或后志,归袝志,迁袝志,盖石文,墓砖记或墓砖铭,坟版文(或墓版文、葬志、志文、坟记、坟志、圹铭、椁铭或埋铭),塔记或塔铭,墓碑文或神道碑,墓碣文,墓表,阡表,殡表和灵表(Zottoli 1882: vi-ix)。
晁德蒞的这种文体分类法在中国传统文体学中较为少见。我国文体学起源于先秦,六朝时期文体学走向成熟,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论》首次全面系统探讨了各种文体的性质和源流。其后,《昭明文选》和《文心雕龙》分别从文学选本和骈文文体分类的角度进一步发展了古代文体学。唐宋以后随着古文兴起,文体学研究从以骈体文为对象转移到以古文为对象,“形成古文文章之学”(吴承学 17)。明清两代“辨体”之风盛行,出现了大量选本。明清文体学的突出特点表现为选本与文体学著述合二为一,文章选集和总集如雨后春笋,如明代的《文章辨体》《文体明辨》和《文章辨体汇选》,它们发展出“序题”这种新的文体学形式来专门概述每一文体的体制和流变。清代姚鼐《古文辞类纂》又将明代的“序题”改为“序目”,即把序言、序题和目录合为一体,在介绍文体分类体例和开列分类目录之后,对每一类文体的特点、功用、源流加以辨析说明。《古文辞类纂》将散文文体分为13大类,有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志、箴铭、赞颂、辞赋和哀祭,其中大部分大类又包含众多小类,如奏议类包括表、疏、上书、弹事、论状等小类(姚鼐 1-22)。晚清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大体继承了姚鼐的文体分类法,并进一步做了改进和简化。他将姚鼐的13大类改为11类,去掉赠序,增加了叙记和典志,把传状、碑志合并入传志类,将原与辞赋平行的箴铭、赞颂划入辞赋类作为小类。此外的其他分类曾选与姚鼐相同,但与姚鼐差异较大的是曾氏将这11类散文文体进一步归纳为3大门类,即1、著述类:包括论著类、辞赋类和序跋类;2、告语类:包括诏令类、奏议类、书牍类和哀祭类;3、记载类:有传志类、叙记类、典志类和杂记类(1-3)。《经史百家杂钞》于1860年成书,是晚清最有影响的古文选本之一。晁译第四卷出版于稍晚的1880年,晁氏在编译本卷时,《经史百家杂钞》代表了中国文体学的最新成果。不过,《教程》分类虽有参考但并未直接本自曾选,而是译自康熙年间陈枚编选的应用诗文杂集《留青集》。陈枚先后编选了《留青集》《留青新集》《留青广集》和《留青全集》一系列应用诗文选本。这些选本均载有“古学辨体”一章,分为韵语类、王言类、章奏类、正文类、杂文类、文告类和悼往(亡)类7大类。(3)经过比对可知,陈枚的王言类就是《教程》第一类“出自君主的文书”;奏章类即是晁译第二类“上奏君主或朝廷的文书”;文告类是《教程》第三类“民事函件”;悼亡类为晁译的第五类“关于丧葬事宜”;陈集中的韵语类、正文类和杂文类3大类被晁德蒞合并为一类,即第四类“著述或科举考试的训练”。晁氏对此3类的整合应是参考了曾国藩《经史百家文钞》分类法,曾氏的“著述门”包括3个小类:论著类、词赋类和序跋类,这3小类所辖文献约略等于陈集的杂文类、韵语类和正文类,而晁氏将其合为一类,也以“著述类”命名,与曾书分类一致。由此可见,晁氏参照曾选,将陈枚对中国文体划分的7大类进一步简化为5类。5大类中各自包含的小类晁氏则大体选译自陈集。晁氏的分类法是在充分借鉴中国传统文章辨体之学基础上的进一步整合与改良,他继承了当时国人对文体分类的最新成果,又对其进行综合调整,这是对传统中国文体学的发展,值得重视与研究。
✦
二
中国散文主流:《春秋》三传与古文
(一) 晚清古文
《教程》将“古文”作为中文散文的代表加以译介,这里所说“古文”特指中国古代一种文体形式。秦汉文章多用散文写成,但那时没有“古文”说法,魏晋六朝崇尚形式华丽唯美的骈文,文风偏重绮靡繁复、排偶对仗。唐宋一反六朝文风,去雕饰、尚自然,重回远古风格,如唐宋八家便提倡学习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孟子》、先秦诸子和秦汉文,由此,“古文”这一概念得以确立,并对明清散文写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明清古文及其变体的创作十分兴盛,代表了明清散文的主脉。清中后期桐城派成为晚清散文写作的主流文体,直至清末民初严复和林纾都以桐城派古文家自居,即使与桐城派观念相异的阳湖派也以专治古文名世,属于古文阵营的内部派别。一般认为清中后期虽有阮元、李兆洛、龚自珍等人推重骈体文和经世文,但是古文一直是晚清散文写作的正统文体,尤其是在正统文人与知识分子中间占据独尊的地位。晁氏选译中国散文,准确地依据了当时散文文坛的主流文体形式。
(二) 晁译古文底本
《教程》第四卷编译于19世纪70年代,此时在社会和学堂中有多种清代古文选本流行,如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官修《御选古文渊鉴》、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等,此外清中前期的古文选本还有《御选唐宋文醇》、方苞的《古文约选》、林云铭《古文析义》、顾贞观《古文选略》等,不胜枚举。我们通过比对,认为晁氏编译第四卷的底本为清初康熙年间吴乘权、吴大职编选的《古文观止》,(4)晁氏翻译使用字字对译法,我们通过《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的注释译文来考查晁氏对《古文观止》的翻译策略。传统中国古籍的注释主要有4种形式,第一种是释词;第二是串讲;第三是释词加串讲;第四种是通释全章大意(王力 614-615)。《古文观止》原注包括了全部这4种注释方式,其释词部分又包含注音(如反切、同音字注音等)和释义两类。《古文观止》串讲部分是对每句话的大意进行讲解,而通释全章大意是编者在每篇选文后对全篇进行大意概述。我们将晁德蒞的注释翻译与《古文观止》原文做一比较,可以看到他删去了原注中的注音和每篇的通释全章大意,而主要对原注中的释词进行翻译,并在个别地方选择翻译了部分原文串讲内容。
晁译本“郑伯克段于鄢”共有7条注释,第一条注释正文第一句“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原文注释是“初者、叙其始也。郑,姬姓国。武公,名掘突。申,姜姓国。武姜者,姓姜而谥武也。”原文本句注释属于释词,晁德蒞的翻译是“Familie cognomina Kiang; mulier autem a viro mutuabatur posthumum nomen谥, ideo et Ou appellata”(Zottoli 1880b: 2),意思是“姜”是家族名,亦即姓氏,女性去世后要从她丈夫那里借一个字作为谥号,借字为“武”,因此被称为“武姜”。可以看到原注前半段关于郑武公名字、“初”字和申国的解释均被略去,译文只对最后一句的姜氏进行了翻译。晁德蒞注释从简,只注出他觉得必要的部分。本句他认为姜氏是该文重要人物,需要做注,其他则可删去。但是我们看到他对本句注释并非全照原文翻译,而是面对西方读者增加了原注没有的对谥号的说明文字,指出谥号乃人去世后追赠的名字,而女子谥号需从丈夫那里得来。这种补充解释可以帮助西方读者了解谥号这一重要的中国文化现象。
正文第二句是“生庄公、及共叔段”。原注是“共,国名。段奔共国,故名共叔”也属于释词。晁德蒞译为“Aufugit in Kong; hinc inditum nomen”,意思是他逃到共国,因此就以此字为名。译文中Kong是大写首字母,所以不必译出前半句“共,国名”,读者也能知道这是地名或国名等专有名词。《左传》记载郑庄公一句著名的话“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这句话原注较长:“暱,亲近也。不义于君,不亲于兄,非众所附,虽厚必崩。崩者,势如土崩,民逃身窜,直至灭亡。较自毙自及更加惨毒矣,而子封终未之知也。”晁德蒞只选译了对《左传》正文的直接解说(引文加粗部分):“Expers justitiae in principem et familiaritatis in fratrem, non habebit sibi addictam multitudinem, adeoque peribit”(Zottoli 1880b: 3),略去了原注渲染添加的串讲部分。
通过原注与晁译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他翻译《左传》的基本特点是1、 以简练为上,原注中注释远比《左传》原文篇幅长,几乎每句都有释词和串讲,但晁氏只从中选择了7条,并经过删改。2、 晁德蒞注释的着眼点在于正文文字训诂,主要是对疑难字词和文化知识进行解释,其选译大都集中在原注释词上,对大量原文串讲则较少翻译。3、 细审《古文观止》原注串讲可知其对原文文意具有较大引导性。在“郑伯克段于鄢”中,串讲多次点出郑伯城府极深、用心险恶,如“(庄公)唯恐其不行不义,而欲待其行也。庄公之心愈毒矣[……]”,又如“庄公实欲杀弟,而曰自毙,曰自及,故为段自作自受之语,毒甚”(吴楚才、吴调侯 2)。其后,又在通释全章大意中再次点明此意,可谓再三致意。《古文观止》如此串讲,用意在于点出春秋笔法,明晰微言大义,这本是孔子作春秋的原旨,将高度的寓意寄托在历史叙述中。但是在晁德蒞看来,这些微言大义并不重要,从而将其全部删去,他向西方读者展示出来的主要是汉语语文学和古文文体意义上的散文文类。
(三) 晁译古文的选编
《教程》对中国历史著作的翻译主要集中在第三和第四卷,第四卷以春秋三传为代表。但是,晁氏选译三传的目的并非是要译介周代历史或中国哲学,而是从古文(Antiquae Prosae)这一文体角度进行翻译。在三传译文前言中,他说“学习古文的士子们要长期研读”《左传》(Zottoli 1880b: 134)。晁氏将三传译为Tres Memoriae, Memoria, 有回忆和历史记载的意思。在序言中,晁氏还介绍三传是孔子编年史的3种评注,《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名称分别来自其作者左丘明、公羊高和谷梁赤。其中,《左传》在三传中地位最高,因为《左传》的文风最为精炼雄辩(expolitissima elocutio)(iv)。可见,晁氏在谈论《左传》优点时也是从文体风格的角度进行评价的。
晁德蒞翻译《三传》的底本是《古文观止》。目前通行的中华书局版《古文观止》整理底本为清乾隆年间映雪堂刻本。我们用中华本与晁德蒞译本选目做一比较可知,《古文观止》中的左传篇目被晁德蒞全部收入,但是晁氏又另外补入了21篇《左传》选文,它们是第十二篇“荀息传奚齐”,第二十一—二十四篇“秦人入滑”“晋败秦师于殽”“楚世子商臣弑君”“甯武子来聘”,第二十六篇“赵盾弑其君”,第三十九—四十二篇“郑杀大夫公孙黑”“齐侯请继室于晋”“楚椒使举如晋”“石言于晋”,第四十四篇“楚太子建奔宋”,第四十六—五十六篇“晏子论梁邱据”“吴入郢”“秦师救楚”“夹谷之会”“吴许越成”“楚子轸卒”“吴将伐齐”“卫侯会吴于郧”“会于黄池”“楚白公之乱”“越灭吴”。《古文观止》所选3篇“公羊传”晁德蒞都进行了翻译,但其中《谷梁传》的2篇他只选译了“虞师晋师灭夏阳”。《谷梁传》的“郑伯克段于鄢”被舍弃应是因为该故事已收在《左传》之中。晁德蒞还调整了原《古文观止》的选目顺序,他将三传集中在一起,共计60篇。
《春秋》三传之后,晁氏又编译了100篇历代散文,这些散文几乎全部选自《古文观止》。但是由于《古文观止》的举业倾向,其选文基本划定在儒家范围之内,而晁德蒞选文视野更加宽泛。他在“周文”部分加入了一篇道家经典散文,即《庄子》的“养生主”,也就是著名的庖丁解牛故事。晁氏选译《庄子》是由于他参考了《经史百家杂钞》,曾国藩出于桐城派而又不守师法,在“姚鼐义理、词章、考据外,添加‘经济之学’;论文则于《史》《汉》、韩柳外,补上庄骚、汉赋”(陈平原 182),兼收并蓄、气魄宏大。曾氏《经史百家杂钞》选入了《庄子》若干篇,其中就有“养生主”。《教程》选文的特点总结起来有三:1、厚古薄今,他较少删除讲述先秦的文章如《国语》《战国策》等,因为这些文章与《教程》卷二和三的四书五经联系较为紧密,可以对其补充对照。也许正因为此,他很少选译《史记》中的西汉历史,删掉了涉及项羽、刘邦和楚汉之争的篇章。2、众体兼备,晁氏注重对中国古文文体的展示,对《古文观止》中各种文体如论、策、疏、书、序、召、传、论、赞、表、楚辞、骈文等尽量每类文体都选译一至数篇。3、名家名篇,晁氏选文注重名篇,如“太史公自序”、诸葛亮前后“出师表”“兰亭集序”“藤王阁序”“陋室铭”、前后“赤壁赋”“岳阳楼记”“报刘一丈书”等历代名篇均选入译本。晁氏也注意各大家的均衡,较少遗漏名家,除了八大家均已入选外,其他如贾谊、司马相如、陶渊明、李白、王勃、杜牧、范仲淹等散文大家都基本入选。
(四) 晁德蒞对古文文体的认知
晁氏在古文译文前言中认为:以往各时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被称作“古文”,与当下的“时文”(八股文)相对。古文的风格并没有过时,反而其雄辩的文风应该被所有士子学习和模仿。学习者反复揣摩研究这些文选,在研读四书五经的同时,他们也十分愿意挑灯夜读这些文献。他们沉浸在历代大作家的文选之中,这些作品很多比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的演说词还早,它们体现了作者多种多样的天才,选文百家争鸣(Zottoli 1880b: 134)。晁氏准确区分了古文与时文这两种晚清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散文文体,并认识到古文在中国读书人中受到普遍重视。他将中国古文与古典拉丁散文修辞与演讲术的最高典范西塞罗相提并论,足以显示出他对古文价值的认可和看重。
晁氏选择《古文观止》作为翻译古文的底本,既是因为该书为晚清学校常用教材,影响较大,也是看重该书选文范围宽广,兼顾先秦至明代各时期散文,包含各类文章体裁与艺术风格,篇幅又较为适中等优点,而其他选本或失之于卷帙浩繁(如《御选古文渊鉴》),或有选文范围狭窄之弊(如《唐宋文醇》),或选本流传不广(如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晁氏选译此书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古文观止》与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关系密切。清代古文家早就“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 (郭预衡 610-611),此“时文”即指八股文。《古文观止》的选评者吴乘权便“工举业”, 该书出版前其实为选评者教授八股文写作的讲义,其选文、注释和评点大都是以训练写作八股文为中心展开。《教程》第五卷翻译了大量八股文章,认为八股文是当时中国有代表性的文章种类,他在卷五全面译介八股文之前,先在卷四将训练八股制艺的《古文观止》和作为八股文渊源的古文加以翻译,无疑符合学习中国散文的教学步骤。可见晁德蒞选译《古文观止》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体现了他对中国散文文体风格发展,以及古代汉语教学与习得的深刻理解和认识。
此外,晁德蒞选译《古文观止》的缘由还在于该书选文分类较其他文选更有优势。晁氏在第五卷前言里较为忠实地译介了中国传统的文体分类法,但是传统中国文体学也有划分模糊、分类异常繁琐的弊病。《古文观止》作为清初一部古文选本,没有像《古文辞类纂》与《经史百家杂钞》那样以文体划分编排全书,而是以年代顺序安排所有选文。“时代为经,作家为纬”(张涤华 66),打破了《文选》以降中国散文选集多以文体进行分类排序的传统。时间顺序的编排体例不仅避免了将同一作家的作品分散到各个文体的弊端,也可以使读者获得对中国散文发展史全面而清晰的了解。对于西方读者来说,这种历时编排法显然比文体分类法更为简单明了,易于接受和理解,这也符合西方文学选集的常用编排体例。此外,从五卷本全书来看,年代分类法与《教程》全书体例相一致,形成了从四书五经等先秦经典(卷二、三)、到历代散文、诗词(卷四、五)再到明清小说、戏曲(卷一)的中国文学完整的发展脉络,体现了晁氏的文学史意识。另一方面,《教程》在卷五前言中又对中国散文文体做了全面的译介,作为补充资料供西方读者参考,使共时文体分类与散文历时发展相得益彰,可以说是颇为周到的设计安排。
✦
三
应用性散文:历代尺牍
《教程》在160篇历代散文译文之后,另翻译了130篇历代简牍作为后续。简牍亦即今日所谓书信或信札,“简”即写于竹简上的书信,“牍”是写在木版上的书信。中国写作书信的传统源远流长,先秦时期就已出现,长期作为一种实用文体用于军事、政务、私人交往等多个社会领域。汉末六朝时期,简牍的文学性逐渐加强,使其在保有实用功能的同时,又兼具文学审美特点,如文学选集《昭明文选》就专门开列“书”(简牍)作为一种文学类别,简牍写作也蔚然成风。唐宋士大夫十分重视简牍写作的政治功能,大量尺牍专集于宋代开始出版。明清是尺牍选本的兴盛时期,专选明朝尺牍的选本与广选历代尺牍的选本均不在少数。清初王元勋的《明人尺牍小引》便说:“自前明以来,选者数十家[……]”(赵树功 70-72),流传至今的有明代杨慎《赤牍清裁》、王世贞《尺牍清裁》、凌迪知《名公瀚藻》、沈家胤《瀚海》、钟惺《如面谈》《文学大尺牍》《文辞大尺牍》等;清初则有李渔《尺牍初征》《古今尺牍大全》、周亮工《尺牍新抄》等(王世伟 142-146)。晚清随着官方与民间邮驿网络的发展,尺牍写作与结集出版越发兴盛,道光年间吴修编辑了汇集有清一代尺牍的《昭代名人尺牍》,光绪年间出版了《曾文正公家书》,《申报馆丛书》也收录有“尺牍类”文献(邹振环 177)。尺牍还与古文关系密切,《古文辞类纂》和《经史百家杂钞》都将书札列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晁德蒞尤其重视尺牍文体,在上述对中国散文文体的5大分类中,他将书信体作为5大类之一单独划分。晁氏重视书信体散文的重要原因应与西方书信文体学蔚为大观有关。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以降,西塞罗、塞内加(Lucius Annaeus Seneca)、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 23- 79)等人的拉丁文书信以及希腊诸家书信成为人们学习写作的范本,出现了书信范文的汇编与文集,讨论和训练书信写作的著作也大量产生,以至形成了专门的学科,即“文书书写术”(epistolography)(克里斯特勒 264-265)。在西方,无论是教会还是政府都需要大量精通书信写作的文书或书记员来处理法律、行政等事务。如弥尔顿、哥德尔密斯等众多饱读古典文献的人文主义者实际上都充当着政府书记的职位。晁德蒞在徐家汇就曾担任教区会议的书记员,因此他精通、重视书信文体也就不难理解了。此外,书信在19世纪的中国和西方仍然是人们日常生活与工作频繁使用、不可或缺的文体形式,现保存下来的在华传教士用于与西方世界联系而写作的大量书信便说明了这一点。晁德蒞编译尺牍大体将其看作一种实用文体,他翻译尺牍的底本《留青集》即是康熙年间影响广泛的应用诗文选集。编选者陈枚先后编选了一系列应用文选本(见上文),其后他编选的《写心集》才“更强调文艺性”(陆学松 79-80)。晁氏将“简牍”译为“书信体”(Stylus Epistolaris),编排在文学性散文——“古文”之后,以示应用体散文与文学性散文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古罗马时期即将散文分为艺术散文(或雄辩散文)和平实散文,艺术散文雕琢精细,而语言简洁质朴的平实散文有时就指拉丁文书信(如普林尼)。这或许即为晁氏将中国散文编译为古文和尺牍两大类的参照。《教程》在简牍译文之后另附了30页篇幅的尺牍写作格式与用语介绍,包括1、 公务书信格式(officiosae schedulae schema);2、 书信中事物的修辞性表达(exornatior rerum nomenclatio);3、 官员称谓(multiplex magistratuum appellatio)和4、 日常书信格式(communis epistolae forma);四项中每一项又各自分为众多小类,资料详实、便于利用,这也充分说明了晁德蒞编译尺牍文献的实用主义考量。
晁氏简牍译文的序言认为简牍大体有两类,家庭成员之间的书信称为“尺牍”,公事往来的信札称为“公牍”。他将公牍再分为三类,即1、 与地位较低人的公牍(ad inferiores);2、 与地位较高人的公牍(ad superiores);和3、 与地位相仿人的公牍(ad aequales)。第一类若在司法领域便称作“札”,如果去信目的为不同意判罚的,称为“批语”;如果表示驳斥,则称为“驳语”。第二类叫做“详文”,包括“照详”“照验”“看语”和“条议”,从厅到府的公牍称为“牒文”,从县到府称为“申文”或“禀帖”。第三类叫做“移文”“咨文”和“照会”。晁氏介绍说,在公牍的开端处会展示该公牍属于哪一种类,如“为札知事,为札饬事,为转饬事;为照会事,为照复事,为恭录照会事;为详报事,为申请事”(Zottoli 1880b: 460)等,使人一见便知该公牍的性质。他还介绍了公牍结尾处的通用格式,如“合行札饬札到该县即便遵照勿违特札,合再转饬札至该县即便知照特札”(461)等。晁氏认为一些尺牍用词独特,有口语演讲的风格特点,这要求用语明晰(perspicuus)、有力(nervosus),并且生动,以达到可以启发并说服读者的目的。
由于尺牍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功能性,不同种类的尺牍往往拥有固定的形式和用语,也就是具有独特的文体,因此,尺牍的文体划分是对其进行分类的核心问题。在序言末尾,晁氏介绍了中国尺牍的全部传统分类,多达50种,包括君谕类(Epistola principis subdito)、臣启类(Subditi principi)、辞命类(Reguli indicentis)、游谈类(Ministri excurrentis)、宦途类(Magistratum exercenti)、将职类(Strategum agenti)、除授类(Promoto magistratui)、议政类(Edisserentis regimen)、酬谢类(Grati beneficio)、庆贺类(Gratulationes facientis)、馈送类(Dona mittentis)、谢馈送(Gratias agentis)、求索类(Aliquid poscentis)、辞却类(Aliquid recusantis)、请召类(Ad convivium invitantis)、期约类(Condictum significantis)、邀请类(Ad aliquid advocantis)、关节类(De re transigentis)、求荐类(Petentis suffragium)、荐举类(Suffragium proponentis)、浼托类(Negotium imponentis)、劝谕类(Ad aliquid hortantis)、慰安类(Consolationem afferentis)、吊慰类(Luctum levantis)、答吊慰(Consolatori respondentis)、家庭类(Patris filio)、与友类(Intimo amico)、褒谕类(Egregia laudantis)、问候类(Salutationem mittentis)、怀仰类(Hominem desiderantis)、久别类(Diu separati)、赠别类(Munere valedicentis)、恨别类(Dissidium dolentis)、谕文类(Edisserentis eloquentiam)、谕学类(Tractantis disciplinam)、求文类(Petentis lucubrationem)、答求类(Petenti respondentis)、志隐类(Secessum cogitantis)、隐乐类(Secessum oblectantis)、谕物类(Corporea disserentis)、激励类(Excitantis animum)、诘责类(Objurgantis culpam)、僧家类(Budhae bonzio)、道家类(Rationis flamini)、四六类(Epistolae numeris ligatae)、详文类(Relationis genus)、牒文类(Denuntiationis genus)、申文类(Expositionis genus)、禀帖类(Significationis genus)、照会类(Certificationis genus)(Zottoli 1880:462-463)。在考察了多种中国传统尺牍选本分类后,笔者认为晁氏如此详尽的分类法在古代尺牍选本中极为少见。
晁译简牍正是将130篇尺牍按上述50种分类进行编排,可以看到这种编排方法不同于译介古文时的时间顺序,而是按文体分类。尺牍选文包括从秦始皇直至晚清的信札,是对中国尺牍较为全面的译介。在这50种分类中,比较特别的是列入了僧道两类,涉及宗教事务。“详文类”实际为政府公告,包括清代康熙年间黄六鸿的《擒获大盗详文》,述及其治内豪强聚众杀人一案,该文载于他的《福惠全书》。嵇永福的《禁溺女典妇详文》是其任浙江严州府(今杭州西南)官员时禁止溺杀女婴、典卖妇女的公文。西方传教士一直对中国杀婴的习俗十分关注。其他还有周亮工《详禁擅取铺行物件》,王际有《窝引逃民事》,王仕云《讨蠹究脏事》等。照会类尺牍10则分别是《大法钦差上任》《大英钦差授任》《恭亲王照覆》(3件)《大德钦差署任》《王大臣照覆》《大美参赞卸任》《提督照会知县》和《知县照会绅董》。(5)其中有法、英、德、美使节来华履职和卸任的照会,以及恭亲王的回复,这类关于中外关系和中西政府间往来的照会在传统尺牍选本中比较少见。《教程》中涉外照会编译自其时刚刚出版的《星轺指掌》(1876)。该书系由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带领同文馆学员选译自德国马尔顿斯(Charles de Martens)所著的法文著作《外交手册》(Manuel diplomatique)。这是中国第一部翻译西方近代外交制度的书籍。该书附录的公文程式有国书两件、照会8件和信函5件,《教程》将照会部分全部收录翻译。外方致中方照会应为中西文一式两份,由外方先撰写法、英、德语文本,再翻译为中文文言,后丁韪良译书时将其收入《星轺指掌》。再后,晁德蒞编译本卷《教程》时再将中文译本回译为拉丁语。从文体的角度来看,外交照会有固定格式,如落款称谓、时间,正文中的顶格、空格、另起等,但是《教程》并未保留照会的特殊格式,他不仅将署名和时间删掉,而且把每件照会全文排为一段,从而使文体格式与全卷中文散文的排版格式相统一。晁氏只重视尺牍的内容,这样便对文体特点有所损耗。最后2件照会《提督照会知县》涉及同治陕甘回乱;《知县照会绅董》有关上海县交还万福宫庙宇及丝茶公所房产事宜,晁氏说这两种照会正是当时中国人日常应用的文书形式,文体简洁而独特。
✦
四
晁德蒞对中国文体译介的卓越贡献
20世纪以前,西人对中国文献的翻译主要以四书五经等中国经典,以及戏曲、小说和诗歌为主,不太注意对散文文类的译介。这里的散文取狭义的散文概念,因为在明清古文文体分类里,六经皆是散文文体,而以现代观点来看,散文的范畴也已扩大到包含诗歌之外的各种书写。明清来华传教士和西方学者、外交官在中外官方与民间交往中也曾翻译了一些中文文书,如康熙通谕、大清法典、清廷与欧洲王室、教皇间的通信、条约、通商函件等,这些散文体文献翻译不过是以实用为目的的零星译述,所译也基本是应用文献。西人对中国文献的分类也存在类似情况,如雷慕沙将中国文献分为3类,除四书五经为“古典体裁”外,科举八股文及类似论文属于“文学体裁”,此外训令、布告等政府文书被划为“文牍体裁”。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则增加了“商业体裁”和更接近口语的“通俗体裁”。(6)因此,西人对中国散文体文献的划分以实用文体为主,认为文学体裁只以八股文为代表,他们对艺术性较高的文学散文极少有专门的译介。如晁德蒞这样大规模翻译古文与尺牍,几乎用拉丁文全译《古文观止》的译著是空前的现象。晁译之后,西方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出现了对中国古代艺术散文比较成体系和规模的翻译。(7)因此晁氏的译文是西方对中国艺术散文的最早专译,其中很多篇什均为首次译为欧洲语言,如对《战国策》《国语》的选译,(8)以及《史记》和古文的译文便是如此。(9)
西人忽视中国散文文体的原因主要在于传统西方文学文类划分一直以诗歌、小说和戏曲三分法为主。西方文类学起源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10)其中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前384-前322)《诗学》将古希腊文学分为抒情诗(日神颂和酒神颂)、史诗与戏剧(悲剧和喜剧)3类,在文学中并没有为散文留有位置。他认为散文是一种演说术,而非文学。此后直到现代,西方的文类划分大体没有超出亚里士多德的范围。虽然后代文体有所发展,讽刺诗、田园诗、训教诗等各种诗体加入诗歌大类,正剧等加入戏剧,史诗由小说代替,但是古罗马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的《诗艺》、文艺复兴诗学、18世纪百科全书派,以及黑格尔《美学》等西方历代文类讨论几乎都将散文摒弃在文学殿堂之外。直到20世纪中叶,西方文论的权威著作韦勒克(René Wellek)的《文学理论》在“文学的类型”一章中仍然几乎没有涉及散文。这并非是说西方没有散文写作传统,恰恰相反,从古希腊的演讲文、史哲著述、西塞罗演说、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的军事史、中世纪布道文、圣经翻译、蒙田(Michelde Montaigne)、培根(Francis Bacon)散文等历代杰作层出不穷,但是在西方理论家的论述中,这些都不算作文学,它们只是哲学、历史著作,是实用文体而已。(11)这种根深蒂固的文类分类法使西人在译介中国文学时往往对散文视而不见,尽管中国散文文类异常发达,中国人对文章之学格外重视,但明清时代的西人大都仍以西方传统文类观念看待和译介中国文学。(12)
一般认为,晚明以来传教士翻译中国文献起于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高母羡(Juan Cobo)翻译的《明心宝鉴》,这是一本三教合一的幼童启蒙格言集,有明一代流传甚广。此类格言类童蒙和劝善书在明清中国不胜枚举,如《菜根谭》《小窗幽记》《增广贤文》等皆属此类。传教士选择翻译此类书籍,除了其流传广、内容简单易学、便于概括了解中国文化等原因外,另一重要的文体学缘由是西方自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流行格言作品,《圣经》中亦有所罗门的《箴言》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流行格言体书籍,如著名的文艺复兴三大格言集,包括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的《箴言集》和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iardini)的《格言集》,其中《智慧书》的作者巴尔塔沙·葛拉西安(Baltasar Gracián)即是西班牙天主教传教士。几乎与高母羡同时,罗明坚翻译了《四书》。随着利玛窦将耶稣会传教策略调整为批佛补儒,《四书》翻译成为了焦点,从罗明坚到《中国哲学家孔子》出版的近百年中,几代传教士认为《四书》是中国最为核心的文献。其次,传教士从金尼阁始便展开了五经及《孝经》的翻译工作,并认为这也是中国经典著作(Libri Classici)。卫方济(Francisco Noël)的拉丁文《中华帝国六经》与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的法文《中华帝国全志》参考、集结了前辈传教士译文,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当时西人对中国文体的认知。杜赫德在其书中编入了小说、元杂剧,以及唐顺之、徐乾学等编辑的古文选,是晁德蒞之前西人对中国散文最大篇幅的翻译。其中从唐顺之文选中译有1篇欧阳修、3篇苏轼的散文,杜赫德将这些文学作品与康熙御选朱批、《列女传》和王阳明语录并列在一起。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上半叶陆续出版的16卷本法文《中国杂纂》是众多传教士译著的合集,向西方全面展示了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文类的认知,其中包括四书五经、《孝经》、康熙和雍正的《御制文集》选、格言谚语选、杂诗和散文。散文部分翻译了如《古文观止》的“陈情表”等,(13)但《中华帝国全志》与《中国杂纂》所选译的杂诗与散文数量很少,而分类体系又较为庞杂。他们将中国文学与其他中国文献,如史传、《大清会典》、兵书、宋明理学著作、《本草纲目》等排在一起进行编辑,这主要体现出编者所具有的巴洛克式和18世纪百科全书式的编辑分类法,(14)对散文文体则谈不上有何深入见解。
马若瑟是明末清初老耶稣会传教士中公认中国文学最为博学的人物之一,在他的《汉语札记》中,他根据成书时间、可信度和作品风格把中国著作(包括散文)分为9大类。第一类为经书,包括《易经》《诗经》《书经》;第二类是《四书》《春秋》《礼记》;第三类为《道德经》《庄子》《山海经》,十三经中的《周礼》和《仪礼》;第四类有《楚辞》《列子》《关尹子》《荀子》《太玄经》,最后又重复列了《孟子》;第五类是春秋三传、《国语》《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说文解字》《通志》;第六类为八大家中的韩愈、三苏、王安石、曾巩和欧阳修,但是未见柳宗元;第七类为经典注疏家,有孔安国、孔颖达、王肃、毛苌、郑玄、王弼和朱熹,以及康熙《日讲》和《周易折中》;第八类是宋明理学,包括《性理大全》,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和邵雍;最后一类是史传。(15)我们看到虽然马氏涉及的中国文献较多,但是他的分类相当凌乱,不同体裁的书籍被分为一类。其中虽然有对唐宋散文的介绍,但是囿于该书的体裁,并没有对散文本身进行翻译。此书手稿一直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直到19世纪初才得以出版,马氏的《汉语札记》也是晁德蒞编译本书时的重要参考文献。
另一方面,新教来华后对中国文献也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如马礼逊、麦都斯等分别翻译了《三字经》《大学》《孝经》《书经》等经典和《三教源流》《太上老君》《戒食牛肉歌》等民间宗教书籍。伟烈亚力的《中国文献纪略》仿照《四库全书》经史子集体例编写,本质上是一本中国文献目录。其书只对《文选》《文苑英华》等少数文集做了极简短的介绍,该书Essayists部分置于子部,内容主要为笔记、文言和白话小说,大致对应《四库》小说家部分。(16)理雅各是译经的集大成者,他译有四书五经、《竹书纪年》《佛国记》《道德经》等,但几乎未译散文及诗歌,他的译介主要集中于中国核心经典。与晁德蒞同时的俄国汉学家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献史》(1880)专设了中国美文学一章,不过在3页的篇幅中仅介绍了科举和赋体,文集如《文选》《皇清文颖》等只略提及书名而已。(17)除此之外,近代西人在对西方收藏的汉籍进行分类时,基本也只将中国文学划分为诗歌、小说和戏剧三大部分,与西人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大体相同。雷慕沙(Abel-Remusat, 1788-1832)、儒莲(Stanislas Aignan Julien, 1797-1873)、大巴赞(Antoine Bazin, 1799-1863)、德理文(Le Marquisd Hervey de Saint Denys)等法国汉学家在中国文学领域重点译介了《四书》《书经》《老子》、唐诗和中国小说戏曲,英人帕西、德庇时等也侧重于对中国小说、戏曲和诗歌的译介。
当时间来到晚清,晁德蒞在继承了前辈传教士和汉学家译著文类的基础上,重点对中国散文进行翻译,其篇幅超过了全集的五分之一,并将散文文体作为与诗歌、小说、戏曲和经典并列的五大文体之一,尚属首次。这是对中国文献,尤其是中国文学文体的全面认知。晁氏将古文译为Antiquae Prosae, 即古代散文。Prosae一词的原形为prorsus, 意思是“直接的”,也用于表示文体,在拉丁文中可以与演说连用,如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就说过“prosa oratio”,意为自由演说,表示一种自由、随意的演说风格(Lewis、Short 1474)。这种说法源自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之后这一词汇进入欧洲各民族语言。我们从上文对西方文类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散文并没有进入西方文学的文类体系,而晁德蒞借助西方文类学知识对中国文学和文献进行了总体分类,分为经典、散文、诗歌、小说和戏曲五大部分,尤其是将散文作为其中一大类,填补了西方两千多年来文类三分法的缺类现象。这无疑是在充分研究中国传统文章学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较为符合中国文学实际的文类划分。另一方面,晁氏开创了中国文学文类五分法的先河,除去其将四书五经作为经典单分一类外,其余四大类与现代学术对中国文学的文体分类完全一致。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文学文类现代四分法是中国学者在西学影响下经过漫长的摸索才逐渐确立的。这一探索要晚至20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才开始进行,如刘半农、傅斯年、朱自清等人在1920年代都对四分法有所讨论,1935-1936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明确将新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4大类,“四分法遂被广泛接受”(宋莉华 178-179)。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晁德蒞在此前40年,也就是1880年前后在上海土山湾出版的《教程》中即提出包含四分法在内的中国文学、文献分类体系,这对中国文体学和文类学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学界进一步研究探讨。
✦
往期推荐
学术观点|郝岚 :“后理论”时代的新世界文学
学术观点|莫亚萍:阿普特翻译研究转向——从不可译到修复性翻译
学术观点|叶舒宪:变:作为新文科探索先驱的中国比较文学
学术观点|李玉良:《论语》翻译与美国当代政治哲学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完)